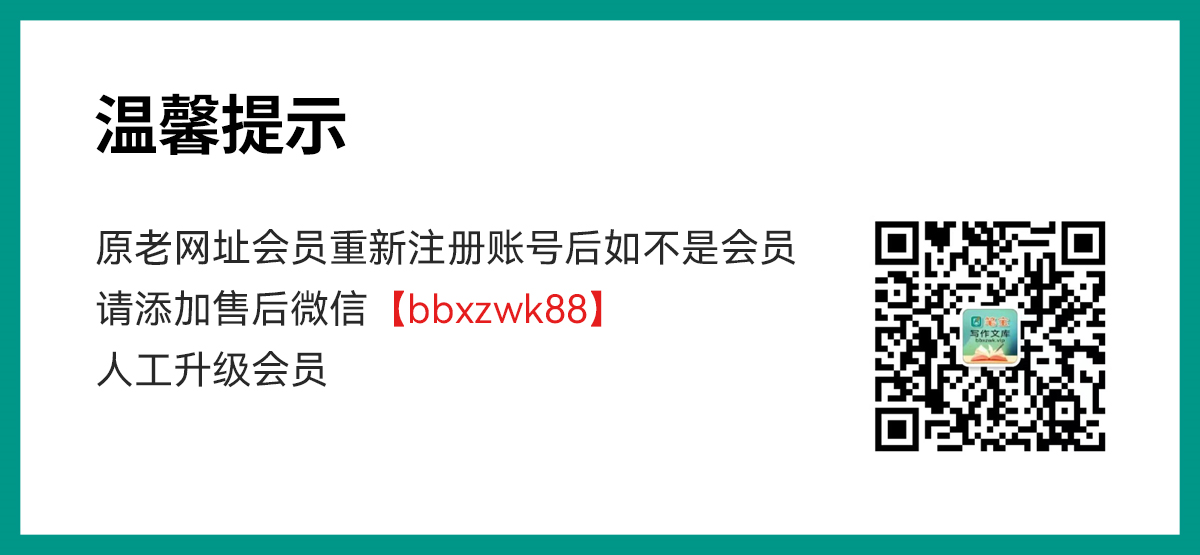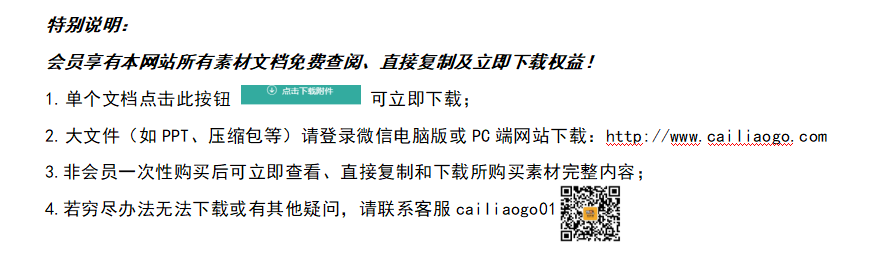从《藏书》《续藏书》看李贽的史学理念
《藏书》《续藏书》是明代李贽的主要著作。李贽一生写下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他最重视的是《藏书》,自称“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爰之书”。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宜,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故取名为《藏书》。
《藏书》共68卷,取材于历代正史,用纪传体载录了自战国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800名。李贽按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类目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或简短评语,评论尖锐、泼辣,富于批判精神。《续藏书》为《藏书》的续集,由王维俨于李贽去世7年后刊,共27卷,主要取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载录了明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约400名。《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对史书体例和编排进行了创造,对载录的历史人物做了与传统见解不同的评价,集中体现了李贽的史学理念。
昭彰事实,垂鉴后世:对史书体例的创造。李贽在史学理念方面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从经学“袪魅”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经与史相为表里”,主张历史学研究应史论结合,注重揭示兴亡治乱的规律,以更好发挥其“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社会功能,为“志在救时”的实践目的服务。遵循着史论结合、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思路,李贽在史书体例上有一个重要创造,即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造“世纪”体。这一创造,打破了传统的“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本纪”体例,有利于人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的启迪。一方面,那些虽然失败却影响过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纷纷被写入了“世纪”中。如陈胜和项羽,李贽专门为其写了传记《匹夫首倡》和《英雄草创》。另一方面,《藏书》《续藏书》着重记叙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帝王的事迹,不是任何帝王都可以在“世纪”中占有一席之地。如西汉,主要记述了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5位帝王的事迹,至于元、成、哀、平诸帝,则被认为“此不足称帝矣”,附于宣帝之下一笔带过。
《藏书》的列传部分也与传统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在分类上有很大不同,其列传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大类。从《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的说明来看,列传各类编排的顺序,即形成历史由治而乱的过程。李贽认为儒臣为治终乱始的关键,其云:“儒臣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在举用儒臣前,治世有大臣、名臣,无论君王是否为圣明之主,举用大臣便得以辅天下而至太平,使百姓得到安养。名臣虽未必知学然实有学者,凭其才能可至守成治世之功。李贽所谓之儒臣,其功皆在文学,故无益于天下,又以明哲保身处世,故天下无臣之事功,便日渐衰退至乱世。世乱则武臣必出,贼臣觊觎天下,亲臣、近臣谄佞于君臣之间以取其利。天下至于大乱,大臣无所作为,隐于江湖,是以外臣为终。从《藏书》的这一史学体例来看,李贽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总结中国历代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规律性,探求国家富强的道路。
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以事功为主的记载。《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实效为准,而非道学者所依据的圣门古训。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高度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称其为“千古一帝”;他赞赏法家革新进步的思想,给予著名法家人物及具有改革理念的政治家比较高的评价。李贽说:“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己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实学也。”可以看出,李贽的“实学”理念包含了“当行”和“可行”两种属性,体现了“道不虚谈,注重实效”的标准。